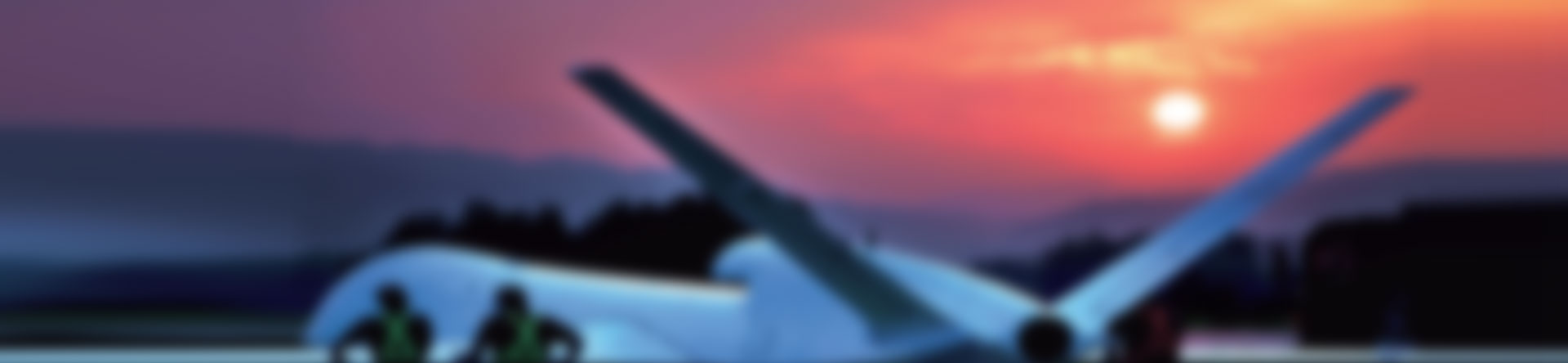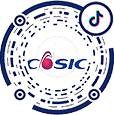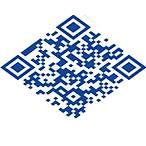当山峦的褶皱浸染六十年月华,在黔北的深山里,星火不眠——灯火长明处手敲计算机的沙沙絮语,暴雨突袭时用身体护住精密仪器的温热臂弯,戈壁滩上仰望利剑划破苍穹的湿润眼眶……这些是属于航天科工十院人的“拾光”故事,都是航天精神、三线精神的多棱镜,折射出"科技强军航天报国"的使命荣光。让我们以故事为舟,溯流而上,打捞那些沉入时光深处的璀璨星辰。
贵州遵义北京路,一座红砖小楼前,一棵香樟树枝繁叶茂。
82岁的乔文礼站在树下说,这是他1974年和同事一起种的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,光影斑驳。60年前的春天,乔文礼从北京抵达遵义时,也是这样一个春意盎然、阳光灿烂的好天气。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,国际形势风云变幻,新中国为做好应对,悄然开始在大后方“备战备荒,深挖洞,广积粮”。
无数青年响应党的召唤,告别熟悉的城市与家园,奔赴前路未知的山区。乔文礼、袁运生、唐守桥,这3位互不相识的陌生人,就这样从不同的起点,走向了命运交汇地——贵州遵义。
进山,去国家需要的地方

1965年春节刚过,只有21岁的乔文礼就离开了北京。“命令一下,就要服从,没有任何条件。”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道。
乔文礼简单整理行装,身着便装,登上了南下的列车。火车一路颠簸,他和数十名同伴肩负特殊任务,“地点是贵州,但具体到什么地方,保密。”
3月2日,乔文礼抵达遵义。“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,下午3点15分。”那一刻,他暗下决心:既然来了就“没有回头路”。年轻的乔文礼并不知道,这一去就是几十年,他将在这里扎根,度过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。
6年后,袁运生也来到贵州。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,接到调令后,他和其他几位同事从上海出发奔赴贵州。
“当时,我们那些参加工作的人,到哪个地方去,全听国家召唤。”袁运生说。
就这样,袁运生告别了上海,投入了黔北高原的怀抱。在之后的数十年里,他和同事们在大山深处,将青春奉献给祖国的航天事业。

青年袁运生(袁运生供图)
相比之下,只有13岁的唐守桥是“被动”来到遵义的。1972年元旦过后不久,他随着父母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从四川宜宾出发前往贵州。他的父亲曾在部队服役,转业后辗转不同的地方。这一次,父亲又主动申请支援三线建设,把全家都带上了。就这样,唐守桥一家六口挤上了一辆大卡车,开始了南下的征程。
“怎么越走越去穷的地方?”年少的唐守桥心里不满。他的弟弟赌气,甚至背起书包扬言要“走回宜宾”去。父母听在耳中,没有责怪。

三线建设旧照
初到黔北,环境是超乎想象的荒凉与艰苦。遵义当时只是一个小城,城内没有几栋像样的楼房。乔文礼等人被安置在市区一座新建成的大楼里,在那栋楼的顶层眺望,四周皆是起伏的青山。
1965年,当川黔铁路试运行的火车第一次驶进遵义时,消息不胫而走,上万名老乡从四乡五里赶来,站满了对面的半山腰。乔文礼也跑到楼顶去看,只见人山人海,甚至有村民抬着年迈的父亲坐在滑竿上,只为让老人看一眼火车。
唐守桥一家初来乍到,感受到更多的是不适和艰辛。那是1972年1月的一个傍晚,载着唐守桥一家的卡车驶入遵义市区时天色已黑,冬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带来刺骨的湿寒。一家人被安排暂住在基地招待所。
当晚,他们只在遵义的路边找到了推车卖的小吃——羊肉粉。唐守桥的母亲平日一口羊肉都不碰,姐弟也跟着不吃羊肉,于是一家人都吃了不带羊肉的“羊肉粉”。“非常难吃。”在唐守桥的记忆里,这顿“贵州第一餐”味道古怪,难以下咽。那一夜,年少的他在异乡的寒夜辗转难眠。
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征程。
扎根,筑起国防屏障

刚到遵义,乔文礼就参与到选址工作中。他们沿着崎岖小路勘察地形,走访当地干部群众,走遍黔北山野,为基地选址。
1965年8月,大批从北京、上海等地抽调的技术人员进入贵州,基地建设全面展开,依山傍水建起办公楼、厂房。
“先生产后生活,先厂房后民用。”三线建设者们住在帐篷里、草棚里。“贵州落雨当过冬”,多雨的贵州让人们在盛夏也离不开被子,白天与夜间的温差很大。冬天更是湿冷入骨髓,夏天蚊叮虫咬不说,还时常有蛇钻到床上、鞋里。
当时由于条件简陋,大家住在用毛竹搭建的4层“超级宿舍”,大通铺中间用竹席隔开,男走南门,女走北门。“可是席子挡不住虱子、跳蚤的‘进攻’。”乔文礼回忆道。
根据《遵义市三线建设志》记载,截至1970年,基地开工建设的生产厂房及设施项目分布在遵义周边的山岭之间,科研人员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,逐步攻克了相关技术难题。
1973年8月,上级部门决定对一型产品进行改进设计。袁运生所在的设计所咬牙攻关,开始了新产品的预研。
彼时,基地既有各生产厂的技术人员、高校专业教师,以及具有试验经验的部队人员。这种跨单位、跨领域的技术组合能否形成系统研发能力,外界持相对怀疑的态度。“因为是第一次研制,你能不能承担总体工作,上级是表示怀疑的。”袁运生回忆说。当时,他是基地设计所骨干,未参与答辩,但对团队实力充满信心。最终,审查结论确认,具备该产品研制能力。
1983年,该产品正式定型,其性能指标大幅提升。

遵义会议召开40周年之际,在新落成的基地机关办公楼前,乔文礼(后排左二)与同事合影(乔文礼供图)
三线建设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有些项目在起步阶段就遭遇了夭折。1974年,唐守桥的父亲回到家中,告诉家人一个消息:他们厂与其他基地的一个厂定位出现冲突,要被调整。一时间,不少职工做起了回原籍的打算。然而唐守桥的父母经过一番思量后作出决定:不回去了,就留在基地。
那个年代,成千上万和唐守桥父亲一样的三线建设者,用质朴的信念诠释了责任与担当。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,曾经人迹罕至的山谷变成了热火朝天的科研生产基地。
转身,闯出一条新路

岁月流转,进入20世纪80年代,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,持续多年的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时期。对基地来说,新的挑战接踵而至:产品订单大幅缩减,企业不得不找米下锅。1990年,如何寻找出路,成为摆在所有三线干部职工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“有些厂因经营困难,厂领导来到基地机关诉苦,眼泪噼里啪啦掉。”乔文礼回忆起这段经历,哽咽着说不出话。“当时的领导这样跟他们说,‘如果眼泪能够解决问题,我们就抱头痛哭吧’。”
转型并非易事。许多工厂开始利用富余产能尝试民品生产。
以唐守桥所在的风华厂为例,为了生存,单位领导班子主动求变,决定开拓民品项目。唐守桥亲历了这场转型。作为一线技术工人,他清楚地记得,从1982年起单位陆续研制了电风扇、印刷机、液氮罐等产品,希望以此打开民用市场。当时车间里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零件,他和工友们既兴奋又紧张,生怕干不好影响了单位前途。
虽然部分产品由于市场原因下马,但也有项目取得成功,印刷机底盘和传动架的订单一度排满了生产计划。到1984年年底,风华厂又大胆开发出自己的知名民品——风华牌电冰箱。这些举措为企业闯出了一条新路。

在转型的同时,基地并没有放弃自身赖以立足的国防科技事业。“那是最艰难的几年。”袁运生回忆,“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,坚持技术创新,在试验场连续度过5个春节。”
20世纪90年代初,他临危受命,走上领导岗位。“必须自己动脑子干这个事儿,再困难都得要克服要搞。”回忆那段日子,袁运生语气坚定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几年攻关,新产品终于研制成功,并顺利通过了上级部门的鉴定。
唐守桥参与了这款产品的生产工作。“当时厂里有3000多职工,我是焊工,专攻关键部件焊接。”他说。

回忆起那些年为赶工期加班加点的日子,唐守桥依然充满自豪:“我觉得我不能干出废品,那是很丢人的事情。”正是抱着“不出废品”的信念,他在几十年的焊接生涯中竟从未报废过一件产品。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维护了14年的老焊机:“那是1965年上海造船厂生产的设备,我把它当宝贝一样,每天干完活都细心保养,一用就是14年。”在他心里,这台老机器不仅是生产工具,更是陪伴自己的战友。
转型年代,有人选择离开,而更多的人选择留下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人才和劳动力产生了强大吸引力。
曾经无怨无悔扎根山沟的三线建设者,到了中年也难免面临现实的考验:是坚持留在三线,还是回到大城市?许多人在矛盾中徘徊,而乔文礼、袁运生和唐守桥选择了前者。
“也可能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好,吃喝玩都方便,但是我们在这里生活也挺好,不愁吃、不愁穿。”袁运生说。
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化推进,地处偏远山沟的老基地逐渐将目光投向山外的世界。彼时的基地虽在自身努力下撑过了艰难岁月,但客观瓶颈依然存在:交通不便、配套不足等制约了进一步发展。进入21世纪初,这项“移山换地”的构想终于变为现实。多年在山沟里扎根的唐守桥也随风华厂搬到了贵阳。


“2015年,我们厂成立50年,老职工回来了大概300多人,从上海租了好几辆大客车开到贵州。”唐守桥接待了他们。他说,来了以后大家都很高兴。“他们当年来的时候住棚子、喝稻田水,现在变化太大了。”
采访结束时,唐守桥建议:“去遵义的话,可以到北京路看看老机关楼,顺便吃碗羊肉粉。”
“羊肉粉好吃吗?”记者问道。
“那是!现在的羊肉粉可好吃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至此,距离13岁的唐守桥吃到人生第一碗“羊肉粉”已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又是一年春天,北京路那棵香樟树在风中舒展枝叶,机关办公楼红砖斑驳,无声镌刻着一段青春往事。